http://hnrb.hinews.cn/html/2011-07/04/content_374141.htm
『海南日报』2011年7月4日 本报记者 陈耿
■这里是琼文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这里更是卧虎藏龙之处
红色之地白石溪
【相片】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的白石溪地区革命烈士纪念碑。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6月30日上午,刚到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东昌农场辖区内的“白石溪地区革命烈士纪念碑”,突然大雨如注,雨点变得又粗又密,拍在身上好生疼痛。这座1991年3月30日落成的纪念碑,碑柱正面的12个大字由书法家郑志聪题写,碑座四面镶有色大理石,正面镌刻的碑文,简明扼要地概括了白石溪地区的历史贡献和地位———
“白石溪地区一九二六年建立党组织,是琼山、文昌地区的重要革命根据地,也是海南省著名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该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赤心报国,为海南人民解放事业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各个革命斗争时期涌现了大批英雄人物,为国捐躯的英烈有359人,被敌杀害的群众有3500人,有40个村庄被敌人焚烧夷平……”
脚下的这片红色土地,承载了太多壮怀激烈的故事。
★革命之地
海口云龙、红旗、三门坡和大坡等地,多是红土地,记者尽管知道砖红壤是火山岩被风化形成的常识,但在听说、记录先烈故事的同时,总会产生这些红土地是被烈士鲜血染红的“幻觉”。好在看见白石溪上裸露的白色石头和潺潺流水之后,这种感觉得以缓解。
原琼山市党史研究室主任王万江告诉记者,白石溪地区主要指白石溪周边地区的树、白石溪、中税和大坡一带,在土地革命时期属于琼山十七区,抗日战争时期归五区管辖,其中树和跟它交界的文昌南阳,是琼文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地带。
1926年,树乡就有了共产党的小组和支部;1928年2月,塔昌村赤卫队主力与邻近各村的数千名农民赤卫队队员,配合红军攻打拥有正规武装的国民党大坡民团,酣战三天三夜。支部书记符志顺带着党员和群众配合赤卫队作战,党员傅楫海、陈有宽、陈有华、陈大书、符树存等,手持铁耙、双筒、长矛、大刀,不怕牺牲,冲入了大坡民团老窝杀开了一条血路,国民党死的死,逃的逃,溃不成军。很快,“树乡苏维埃政权”宣告成立。
正因为是琼崖共产党的战略要地,白石溪地区成了敌人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时刻酝酿对其进行无情打击。“树乡苏维埃政权”成立3个月后,1928年5月,国民党方面很快又纠集兵力扑向树,不少革命者惨遭杀害。塔昌村的交通员符树存被捕时,把党的秘密信件塞进嘴嚼烂吞下,敌人为了捞到党的机密,用铁丝穿过他的脚筋吊着拷打,挖掉双眼,割掉睾丸,其惨状不可忍睹,直至壮烈牺牲。
更悲惨的遭遇是在日军侵琼之后。1942年下半年,日寇动用飞机、装甲车,向琼文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将树划为“无人区”之一,实行“三光”政策,先是从空中轰炸,然后烧杀掠夺,驻扎重兵,截击、屠杀抗日干部和群众;日军还在大坡和树等地施放毒气、毒药,致使许多抗日军民中毒、烂脚和拉稀而死,农作物也因此而枯死。
《中国共产党海口历史》对日军制造的树等“无人区”的记述是:“村无炊烟、路无行人、尸骨遍地、残垣断壁、乌鸦群飞、野草丛生的恐怖世界。”
★藏人之地
一直以为“琼山无山”,可是过了云龙、红旗,逐渐进入南部的三门坡、大坡地区之后,进入视野的却是满目连绵的青山,怪不得当年冯白驹等人会选择在那里打游击战,让敌人奈何不得。
能够开展游击战,不仅靠利于藏匿的群山密林,更需要民众的认支持。
1933年,从母瑞山突围回到琼文根据地后,冯白驹也经常到白石溪地区活动,甚至住在村民家中。有一次,国民党团丁把他围在一块小山林里,狂叫“抓活的”。当时,躲在山林里的一位姓张的农民挺身而出,站到敌人面前厉声喝道:“我就是冯白驹!”团丁们先是目瞪口呆,接着一阵狂喜,大喊:“活捉冯白驹!”
于是,搜山的敌人向张姓农民围拢过来,冯白驹得以脱险,事后敌人才知道上了当。
后来,当地群众筹集了一批光洋,联名向国民党当局证明那位农民是个“疯子”,将他保释出来。还有一次,冯白驹在树乡塔昌村的行踪被敌人察觉,几十个士兵冲进村里,准备抓冯白驹,村民王会生急中生智,挺身而出,乔装成冯白驹跑向树林深处。敌人见状,以为是冯白驹跑了,便一窝蜂地穷追不舍。最终,冯白驹脱险了,不幸的是王会生被捕了,遭受了各种残忍的刑讯手段的折磨,甚至双手双脚都被砍断了,但他宁死不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像这样的经历,冯白驹不止一次遭遇过。因此,他常常语重心长地对身边的战友们说:“要不是人藏人,山能藏住我们吗?”于是,“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成了冯白驹在长期与敌人斗争过程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战胜敌人的法宝。
★英雄之地
在白石溪地区的359名烈士当中,塔昌村的傅烈军特别值得一提。
傅烈军出身贫寒,幼年曾跟父亲种地为生。他练得一身硬功夫,英勇善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尤其是枪法奇准,与林茂松、朱克平、林天和林天贵等人被誉为琼崖纵队“五虎将”。
1932年2月,傅烈军参加琼崖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7月,国民党陈汉光旅过琼“围剿”革命,红军反“围剿”受挫,他随冯白驹等在母瑞山坚持了8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1933年4月,与冯白驹突围回琼文革命根据地后,傅烈军多次伏击、奇袭和围歼敌军,在部队中声望极高。1942年,为粉碎日寇“蚕食”、“扫荡”,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傅烈军在万宁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
傅烈军身上富有传奇色彩。在白石溪地区,尤其是在塔昌村,村民们最津津乐道的是傅烈军的枪法。
在琼崖纵队的一次枪法比试中,每人前面有一根立起的竹竿,谁能先将它打成两半,谁就是胜出者。但见傅烈军自上而下,逐个击破竹节,裂纹如一,开到最后一枪时,竹竿裂开,应声倒地。观看比赛者顿时叫绝不已。
傅烈军总是腰别双枪,作战时也总是左右开弓,而且几乎弹无虚发。有人见过他最犀利的动作———右手持枪击毙敌人后,向左稍稍回身,左手的枪也能击中敌人!
(本报海口7月3日讯)
『海南日报』2011年7月4日 本报记者 陈耿
■这里是琼文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这里更是卧虎藏龙之处
红色之地白石溪
【相片】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的白石溪地区革命烈士纪念碑。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6月30日上午,刚到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东昌农场辖区内的“白石溪地区革命烈士纪念碑”,突然大雨如注,雨点变得又粗又密,拍在身上好生疼痛。这座1991年3月30日落成的纪念碑,碑柱正面的12个大字由书法家郑志聪题写,碑座四面镶有色大理石,正面镌刻的碑文,简明扼要地概括了白石溪地区的历史贡献和地位———
“白石溪地区一九二六年建立党组织,是琼山、文昌地区的重要革命根据地,也是海南省著名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该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赤心报国,为海南人民解放事业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各个革命斗争时期涌现了大批英雄人物,为国捐躯的英烈有359人,被敌杀害的群众有3500人,有40个村庄被敌人焚烧夷平……”
脚下的这片红色土地,承载了太多壮怀激烈的故事。
★革命之地
海口云龙、红旗、三门坡和大坡等地,多是红土地,记者尽管知道砖红壤是火山岩被风化形成的常识,但在听说、记录先烈故事的同时,总会产生这些红土地是被烈士鲜血染红的“幻觉”。好在看见白石溪上裸露的白色石头和潺潺流水之后,这种感觉得以缓解。
原琼山市党史研究室主任王万江告诉记者,白石溪地区主要指白石溪周边地区的树、白石溪、中税和大坡一带,在土地革命时期属于琼山十七区,抗日战争时期归五区管辖,其中树和跟它交界的文昌南阳,是琼文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地带。
1926年,树乡就有了共产党的小组和支部;1928年2月,塔昌村赤卫队主力与邻近各村的数千名农民赤卫队队员,配合红军攻打拥有正规武装的国民党大坡民团,酣战三天三夜。支部书记符志顺带着党员和群众配合赤卫队作战,党员傅楫海、陈有宽、陈有华、陈大书、符树存等,手持铁耙、双筒、长矛、大刀,不怕牺牲,冲入了大坡民团老窝杀开了一条血路,国民党死的死,逃的逃,溃不成军。很快,“树乡苏维埃政权”宣告成立。
正因为是琼崖共产党的战略要地,白石溪地区成了敌人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时刻酝酿对其进行无情打击。“树乡苏维埃政权”成立3个月后,1928年5月,国民党方面很快又纠集兵力扑向树,不少革命者惨遭杀害。塔昌村的交通员符树存被捕时,把党的秘密信件塞进嘴嚼烂吞下,敌人为了捞到党的机密,用铁丝穿过他的脚筋吊着拷打,挖掉双眼,割掉睾丸,其惨状不可忍睹,直至壮烈牺牲。
更悲惨的遭遇是在日军侵琼之后。1942年下半年,日寇动用飞机、装甲车,向琼文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将树划为“无人区”之一,实行“三光”政策,先是从空中轰炸,然后烧杀掠夺,驻扎重兵,截击、屠杀抗日干部和群众;日军还在大坡和树等地施放毒气、毒药,致使许多抗日军民中毒、烂脚和拉稀而死,农作物也因此而枯死。
《中国共产党海口历史》对日军制造的树等“无人区”的记述是:“村无炊烟、路无行人、尸骨遍地、残垣断壁、乌鸦群飞、野草丛生的恐怖世界。”
★藏人之地
一直以为“琼山无山”,可是过了云龙、红旗,逐渐进入南部的三门坡、大坡地区之后,进入视野的却是满目连绵的青山,怪不得当年冯白驹等人会选择在那里打游击战,让敌人奈何不得。
能够开展游击战,不仅靠利于藏匿的群山密林,更需要民众的认支持。
1933年,从母瑞山突围回到琼文根据地后,冯白驹也经常到白石溪地区活动,甚至住在村民家中。有一次,国民党团丁把他围在一块小山林里,狂叫“抓活的”。当时,躲在山林里的一位姓张的农民挺身而出,站到敌人面前厉声喝道:“我就是冯白驹!”团丁们先是目瞪口呆,接着一阵狂喜,大喊:“活捉冯白驹!”
于是,搜山的敌人向张姓农民围拢过来,冯白驹得以脱险,事后敌人才知道上了当。
后来,当地群众筹集了一批光洋,联名向国民党当局证明那位农民是个“疯子”,将他保释出来。还有一次,冯白驹在树乡塔昌村的行踪被敌人察觉,几十个士兵冲进村里,准备抓冯白驹,村民王会生急中生智,挺身而出,乔装成冯白驹跑向树林深处。敌人见状,以为是冯白驹跑了,便一窝蜂地穷追不舍。最终,冯白驹脱险了,不幸的是王会生被捕了,遭受了各种残忍的刑讯手段的折磨,甚至双手双脚都被砍断了,但他宁死不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像这样的经历,冯白驹不止一次遭遇过。因此,他常常语重心长地对身边的战友们说:“要不是人藏人,山能藏住我们吗?”于是,“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成了冯白驹在长期与敌人斗争过程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战胜敌人的法宝。
★英雄之地
在白石溪地区的359名烈士当中,塔昌村的傅烈军特别值得一提。
傅烈军出身贫寒,幼年曾跟父亲种地为生。他练得一身硬功夫,英勇善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尤其是枪法奇准,与林茂松、朱克平、林天和林天贵等人被誉为琼崖纵队“五虎将”。
1932年2月,傅烈军参加琼崖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7月,国民党陈汉光旅过琼“围剿”革命,红军反“围剿”受挫,他随冯白驹等在母瑞山坚持了8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1933年4月,与冯白驹突围回琼文革命根据地后,傅烈军多次伏击、奇袭和围歼敌军,在部队中声望极高。1942年,为粉碎日寇“蚕食”、“扫荡”,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傅烈军在万宁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
傅烈军身上富有传奇色彩。在白石溪地区,尤其是在塔昌村,村民们最津津乐道的是傅烈军的枪法。
在琼崖纵队的一次枪法比试中,每人前面有一根立起的竹竿,谁能先将它打成两半,谁就是胜出者。但见傅烈军自上而下,逐个击破竹节,裂纹如一,开到最后一枪时,竹竿裂开,应声倒地。观看比赛者顿时叫绝不已。
傅烈军总是腰别双枪,作战时也总是左右开弓,而且几乎弹无虚发。有人见过他最犀利的动作———右手持枪击毙敌人后,向左稍稍回身,左手的枪也能击中敌人!
(本报海口7月3日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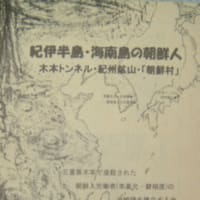
※コメント投稿者のブログIDはブログ作成者のみに通知されま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