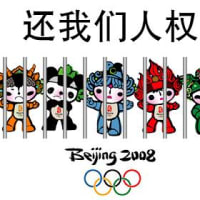陈墨:我同意你的部分意见。1968年冬,我在着手编『中国新诗大概选』,在编辑此期间,我深感在新诗历史上创立“流派”的重要,尤其是我和邓垦的周围,诗歌爱好者越聚越多,而互相影响,爱好与创作出现同一趋向时。为了固化这一相互影响,为了使探索成为凝聚力,也为了形成我梦寐以求的“流派”,我们与1971年编辑了『空山诗选』。探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流派,我们立志高远,眼高于手。但是我们至今并没有形成某一“流派”或“风格”。
王怡:我有异议。陈墨在1964年就自编诗集『残萤集』、『灯花集』、『落叶集』、『乌夜集』,他们的文学沙龙在1971年就将诗集命名为“空山”这个极具朦胧诗意的名字。陈墨的朦胧诗,具有意境。你想可以与徐志摩等人以假乱真。 另外,关于一些成都诗人在当时没有出来,我以为存在一个文化资本的权力问题。我记得廖亦武曾经跟我说过,八十年代初,舒婷陪同美国诗人金斯堡,就是写『嚎叫』的那个诗人来成都,住在成都锦江饭店,当时那是成都最高级的宾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是可望不可及的地方,廖亦武他们一伙很想见金斯堡,他们在宾馆外面转了一夜,进不去,第二天,他们还在宾馆外面死等,希望发生点什么,能够产生偶遇的奇迹,后来保安告诉他们,金斯堡已经走了。北京的北岛们较早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掌握了文化资本的上层资源。文学在当时其实是高度化中央化、资本化、少数人化的。 事实上,陈墨他们没有出来,没有与外界发生碰撞、冲击,因此也就形成一个循环的自闭的状态。在北京出名要比地方上容易的多,外国记者也集中在北京。艺术上的成长也快。 在文学上,陈墨他们其实有两个极端和矛盾的倾向:一个是离群索世,在动乱的年代回归古诗词意境的现代诗歌。比如他们的“空山诗选”。这个特征比后来的朦胧诗更突出。陈墨在1968年10月就有这样的诗句:“蛙声是洁白的一串心跳,寂寞的笺上荡着思潮。五千年的锦水许是累了,载不走这井底孤苦的冷涛”。比起后来的朦胧诗一点也不逊色。 一个是你说的直白式甚至口号式的话语方式。直接介入和批判政治。这个特征也比后来的朦胧诗更突出。比如陈墨写于1976年的《天安门垮了》,就比北岛的任何一首诗都更政治化。除了语言上较少受到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外,我想这也是他们在极端的遁世和极端的愤世之间挣扎,找不到审美上的出路有关。 其实后来八十年代四川出现的“莽汉诗歌”,也与陈墨他们身上的那种上文革体语言的痕迹有某种传承之脉。
刘帮:你们与“莽汉”有怎样的传承之脉?
陈墨:这个我也说不清。这是研究家的工作。与他们中个人有往来,他们出道之前也曾经读过我们的诗歌。
燕子:你们成都有诗歌大刊『星星』,为什么他们没有刊载你们的诗歌?
陈墨:1978年四川的大诗人孙静轩曾经来找过我。同来的还有『诗刊』的雷霆。孙静轩. 还介绍我认识『星星』的几位编辑。由于我生性孤僻,跟这些“道中”诗人没有什么话好谈,我想最终是个性使然吧。
燕子:你们『野草』成员到底是多少?二三十人,太不确定了吧。
陈墨:我也不能说出确定的数字。第一次『空山诗选』上有14人,以后『诗友』和『野草』上更多,投稿者有近百人。 有的很早参加了我们的沙龙,当时他后来或由于种种原因,或加入了官方的作协,他不愿意承认是『野草』的成员;有的人很晚才参加我们,或参加我们的活动并不多,他愿意说自己是『野草』的成员。
王怡:陈墨在农村曾经偷听敌台?
陈墨:文革期间,我是一个卖苦力都无门路的无业青年,我将下乡当作“退役”,只要能够填饱肚子,还能够保 住辛辛苦苦弄来的几箱子书,那就越远越好,越快越好。所以五天之内,下户口走人。那时我有一台收音机,常常偷听台湾广播。那个女播音员姓丁,我被她的声音迷住了,我还写给过一首诗『给丁君』,就是写给她的。
王怡:记得九九曾经跟我说过一个陈墨藏书的故事。1970年,他和陈墨下农村当知青。一天晚上正准备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挖墙打洞的声音,开始还以为是有人偷腊肉,蹑手蹑脚悄悄伸出头一看,陈墨光着身子,满头大汗,在昏黄的油灯下,正用锄头在挖坑。那坑差不多有四尺深。陈墨将从成都带来的书一捆一捆用塑料布包好,放进坑中,他怕命根子一样的书被民兵来搜去,在“坑书”。陈墨的听觉神经太敏锐了,九九微弱的声音都被陈墨听见了,“哪个!”九九只好在暗中亮了相。过了几天,老何的『泰戈尔选集』不见了,他们心想不知道陈墨到底埋了什么宝贝书,于是和老何两人深更半夜去挖陈墨藏书的坑,一个举油灯,一个使劲地挖,,结果泥土挖到底,只有一个大坑和几截烂塑料布,哪里有书!九九把亲眼看到的陈墨埋书的经过又复述一遍给老何听,老何分析说,陈墨他怕你九九到公社告发检举,肯定把书转移了。九九说陈墨确实将书转移了,他怕“运动”临头。尽管他们是患难之交,阶级斗争时期,谁敢相信谁? 我认为这个故事版本,不管放到哪个个时代,放到哪个国家,都同样感人。陈墨他们这些人的一生,就是诗。成都的文学沙龙,不管中国怎样发生怎样的政治、经济变化,持续三十年,这本身就是罕见的史诗。一个时代,应该主流和非主流是并行的,像两根平行的铁轨。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法国十九世纪文学,只知道雨果、巴尔扎克等主流的大文学,实际上,肯定存在过非主流的文学作品,但是我们读不到,原因很简单,没有纪录、记载。
刘帮:『野草』似乎不单单是一个诗歌刊物,还有翻译和文论。比如『马克思捍卫出版自由』,在1979年3月是一篇划时代的文论。
陈墨:这位作者叫鲁连。他读到『野草』的第一期后给我们的投稿。他运用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纪录的辩论』,论述人民必须拥有出版的权利,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制度二者不可相容。他16岁因为写“反动日记”被劳教12年。后来他加入了官方作协,我们都以为他混得很好,其实不然。2003年穷困潦倒中逝世了。
刘帮:这首『天安门』写的是1976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吧。
陈墨:写于1976年清明。据说1979年当局追查『野草』时,成都市委书记一看到第一句“天安门垮了。垮了天安门”,气得发昏。
刘帮:记得日本诗人谷川雁说过,诗人是谁?在不确定得未形成得世界之前,迅速以巨大得力量在人们面前出现。在花朵绽开之前,在萌芽、胚胎得时候就告诉人们,是先知先觉者,这就是诗人。在根的根部,在深层的深层处,在暗的信道,那儿有“万有之母。有存在的原点,有最初的能量。 比如『天安门』,1976年的清明,远在四川成都的陈墨写出了“天安门啊!从那时起,你又穿起了龙袍,又戴上了那光芒万丈的顶翎,从那时起,你就慢慢地变了,变成了宗教的神坛,变成了帝王的国魂”,而在北京的诗人们呢?诗人难道要等到群众街头巷尾、饭后茶余议论的时候才跟在后面发出声音吗?记得黄翔曾经说过,朦胧诗是当局的口香糖。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嚼头。一个时代,连喉咙都被挂上铁锁,朦胧有什么意义?
燕子:一部分学者从文本主义、实证主义出发,质疑文本,质疑“感情记忆”,提出“伪民间”、“伪地下”。并且用现在的审美观评价时代的作品。我以为,我们这一代人评价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为时过早,一个时代也不只有一种文学审美标准。我对主流的、大多数人的合唱总是质疑。我们非常感谢陈墨先生特意为我们送来已经转移到朋友家的保存、珍贵的文学史料。感谢陈墨先生『蓝•BLUE』的信任。更加使我们感到任重道远。你们『野草』每个成员都是一个极为感人的故事,可惜这次时间太短,无法一一采访,请代我们问候邓垦、九九等其他朋友。感谢王怡帮助我们联系、接待。
刘燕子、刘帮整理。陈墨、王怡作了修订 ──
原载 日本双语文学刊物『蓝•BLUE』
Thursday, January 19, 2006
王怡:我有异议。陈墨在1964年就自编诗集『残萤集』、『灯花集』、『落叶集』、『乌夜集』,他们的文学沙龙在1971年就将诗集命名为“空山”这个极具朦胧诗意的名字。陈墨的朦胧诗,具有意境。你想可以与徐志摩等人以假乱真。 另外,关于一些成都诗人在当时没有出来,我以为存在一个文化资本的权力问题。我记得廖亦武曾经跟我说过,八十年代初,舒婷陪同美国诗人金斯堡,就是写『嚎叫』的那个诗人来成都,住在成都锦江饭店,当时那是成都最高级的宾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是可望不可及的地方,廖亦武他们一伙很想见金斯堡,他们在宾馆外面转了一夜,进不去,第二天,他们还在宾馆外面死等,希望发生点什么,能够产生偶遇的奇迹,后来保安告诉他们,金斯堡已经走了。北京的北岛们较早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掌握了文化资本的上层资源。文学在当时其实是高度化中央化、资本化、少数人化的。 事实上,陈墨他们没有出来,没有与外界发生碰撞、冲击,因此也就形成一个循环的自闭的状态。在北京出名要比地方上容易的多,外国记者也集中在北京。艺术上的成长也快。 在文学上,陈墨他们其实有两个极端和矛盾的倾向:一个是离群索世,在动乱的年代回归古诗词意境的现代诗歌。比如他们的“空山诗选”。这个特征比后来的朦胧诗更突出。陈墨在1968年10月就有这样的诗句:“蛙声是洁白的一串心跳,寂寞的笺上荡着思潮。五千年的锦水许是累了,载不走这井底孤苦的冷涛”。比起后来的朦胧诗一点也不逊色。 一个是你说的直白式甚至口号式的话语方式。直接介入和批判政治。这个特征也比后来的朦胧诗更突出。比如陈墨写于1976年的《天安门垮了》,就比北岛的任何一首诗都更政治化。除了语言上较少受到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外,我想这也是他们在极端的遁世和极端的愤世之间挣扎,找不到审美上的出路有关。 其实后来八十年代四川出现的“莽汉诗歌”,也与陈墨他们身上的那种上文革体语言的痕迹有某种传承之脉。
刘帮:你们与“莽汉”有怎样的传承之脉?
陈墨:这个我也说不清。这是研究家的工作。与他们中个人有往来,他们出道之前也曾经读过我们的诗歌。
燕子:你们成都有诗歌大刊『星星』,为什么他们没有刊载你们的诗歌?
陈墨:1978年四川的大诗人孙静轩曾经来找过我。同来的还有『诗刊』的雷霆。孙静轩. 还介绍我认识『星星』的几位编辑。由于我生性孤僻,跟这些“道中”诗人没有什么话好谈,我想最终是个性使然吧。
燕子:你们『野草』成员到底是多少?二三十人,太不确定了吧。
陈墨:我也不能说出确定的数字。第一次『空山诗选』上有14人,以后『诗友』和『野草』上更多,投稿者有近百人。 有的很早参加了我们的沙龙,当时他后来或由于种种原因,或加入了官方的作协,他不愿意承认是『野草』的成员;有的人很晚才参加我们,或参加我们的活动并不多,他愿意说自己是『野草』的成员。
王怡:陈墨在农村曾经偷听敌台?
陈墨:文革期间,我是一个卖苦力都无门路的无业青年,我将下乡当作“退役”,只要能够填饱肚子,还能够保 住辛辛苦苦弄来的几箱子书,那就越远越好,越快越好。所以五天之内,下户口走人。那时我有一台收音机,常常偷听台湾广播。那个女播音员姓丁,我被她的声音迷住了,我还写给过一首诗『给丁君』,就是写给她的。
王怡:记得九九曾经跟我说过一个陈墨藏书的故事。1970年,他和陈墨下农村当知青。一天晚上正准备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挖墙打洞的声音,开始还以为是有人偷腊肉,蹑手蹑脚悄悄伸出头一看,陈墨光着身子,满头大汗,在昏黄的油灯下,正用锄头在挖坑。那坑差不多有四尺深。陈墨将从成都带来的书一捆一捆用塑料布包好,放进坑中,他怕命根子一样的书被民兵来搜去,在“坑书”。陈墨的听觉神经太敏锐了,九九微弱的声音都被陈墨听见了,“哪个!”九九只好在暗中亮了相。过了几天,老何的『泰戈尔选集』不见了,他们心想不知道陈墨到底埋了什么宝贝书,于是和老何两人深更半夜去挖陈墨藏书的坑,一个举油灯,一个使劲地挖,,结果泥土挖到底,只有一个大坑和几截烂塑料布,哪里有书!九九把亲眼看到的陈墨埋书的经过又复述一遍给老何听,老何分析说,陈墨他怕你九九到公社告发检举,肯定把书转移了。九九说陈墨确实将书转移了,他怕“运动”临头。尽管他们是患难之交,阶级斗争时期,谁敢相信谁? 我认为这个故事版本,不管放到哪个个时代,放到哪个国家,都同样感人。陈墨他们这些人的一生,就是诗。成都的文学沙龙,不管中国怎样发生怎样的政治、经济变化,持续三十年,这本身就是罕见的史诗。一个时代,应该主流和非主流是并行的,像两根平行的铁轨。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法国十九世纪文学,只知道雨果、巴尔扎克等主流的大文学,实际上,肯定存在过非主流的文学作品,但是我们读不到,原因很简单,没有纪录、记载。
刘帮:『野草』似乎不单单是一个诗歌刊物,还有翻译和文论。比如『马克思捍卫出版自由』,在1979年3月是一篇划时代的文论。
陈墨:这位作者叫鲁连。他读到『野草』的第一期后给我们的投稿。他运用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纪录的辩论』,论述人民必须拥有出版的权利,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制度二者不可相容。他16岁因为写“反动日记”被劳教12年。后来他加入了官方作协,我们都以为他混得很好,其实不然。2003年穷困潦倒中逝世了。
刘帮:这首『天安门』写的是1976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吧。
陈墨:写于1976年清明。据说1979年当局追查『野草』时,成都市委书记一看到第一句“天安门垮了。垮了天安门”,气得发昏。
刘帮:记得日本诗人谷川雁说过,诗人是谁?在不确定得未形成得世界之前,迅速以巨大得力量在人们面前出现。在花朵绽开之前,在萌芽、胚胎得时候就告诉人们,是先知先觉者,这就是诗人。在根的根部,在深层的深层处,在暗的信道,那儿有“万有之母。有存在的原点,有最初的能量。 比如『天安门』,1976年的清明,远在四川成都的陈墨写出了“天安门啊!从那时起,你又穿起了龙袍,又戴上了那光芒万丈的顶翎,从那时起,你就慢慢地变了,变成了宗教的神坛,变成了帝王的国魂”,而在北京的诗人们呢?诗人难道要等到群众街头巷尾、饭后茶余议论的时候才跟在后面发出声音吗?记得黄翔曾经说过,朦胧诗是当局的口香糖。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嚼头。一个时代,连喉咙都被挂上铁锁,朦胧有什么意义?
燕子:一部分学者从文本主义、实证主义出发,质疑文本,质疑“感情记忆”,提出“伪民间”、“伪地下”。并且用现在的审美观评价时代的作品。我以为,我们这一代人评价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为时过早,一个时代也不只有一种文学审美标准。我对主流的、大多数人的合唱总是质疑。我们非常感谢陈墨先生特意为我们送来已经转移到朋友家的保存、珍贵的文学史料。感谢陈墨先生『蓝•BLUE』的信任。更加使我们感到任重道远。你们『野草』每个成员都是一个极为感人的故事,可惜这次时间太短,无法一一采访,请代我们问候邓垦、九九等其他朋友。感谢王怡帮助我们联系、接待。
刘燕子、刘帮整理。陈墨、王怡作了修订 ──
原载 日本双语文学刊物『蓝•BLUE』
Thursday, January 19,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