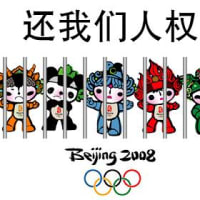燕子:您开书店是什么时候?
陈墨:1983年,我开了一个小书店。那时九九已经定居香港,他给我们几个朋友带回一批原版的新武侠书籍。谁知好景不长,当局突然宣布“清除精神污染”,我被抓进派出所,挨了一顿拳足。幸亏邓垦诸友临危相助,至今终身难忘。另一文友,与我同样的罪名,被关了14个月。
燕子:你们的文学沙龙在谁的家?有无固定的场所?
陈墨:我们成都老百姓一般住的房子很小,没有客厅。一般我们聚集在茶馆。刚才谈到“书市”,后来我们『野草』的几个骨干,比如万一、冯里、谢庄等人就是在那时认识的。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书市”不仅满足了我们的求知欲,而且满足了我们的求友欲。因此,它也成了我们特殊的文学沙龙。风声紧时,我们就转移到离“书市”不远的“饮涛”茶铺,一边照常买书卖书换书,一边谈天说地、评古议今。后来,一些朋友下放当“知青”,我和九九去盐源彝族自治县当“饿农”,我们回成都的时候还是经常去茶馆,新南门的清和茶楼也是我们文革中常常去的地方。在那儿的交换写作的诗歌,讨论阅读的书籍。我自称为“茶铺派”,我的许多诗就是在茶铺里完成的。那时一杯茶才五分钱。五分钱可以泡一整天。
燕子:文革中茶馆没有关门吗?
陈墨:成都这个地方,不管时代发生怎样的政治变故或运动,老百姓,茶,照喝。文革“武斗”中最高潮的时候,茶馆也照开。
刘帮:听说您用卞之琳、李金发的名字写的诗歌,曾经以假乱真?
陈墨:我对朦胧诗的偏爱已久。1968年我着手编撰的『中国新诗大概选』时对“现代派”的收集与学习已经开始,那时也尝试写过朦胧诗,并且题上卞之琳、李金发的名字夹在他们的诗中间,居然还能鱼目混珠,让人莫辩真伪。后来不写了,一是悟到朦胧诗在这块土地上属于早产的贫血儿,且严重的水土不服,更重要的是,是悟到“确立自我、别模仿他人”的艺术真谛。
刘帮:您的老笔记本上的诗歌年月为什么是“1926年”、“1927年”、“1928年”?
陈墨:为避开“文字狱”。免遭杀生之祸。“1926年”就是“1966年”,“1927年”就是“1967年”,“1928年”就是“1968年”。
刘帮:你们大多是笔名,请详细注明你们的真名。再过几十年或百年,后人在研究这段文学史料时莫辩真伪了。
陈墨:我可以注明我们大家的真名。我的笔名除了陈墨、还有秋小叶、一丁、何必、也放等等几十个,一度还冒名徐志摩、戴望舒、朱湘、卞之琳等。或问:“一个苦力有这许多笔名,岂非画饼充饥乎?”答曰:“官方文坛多用本名,――直接受利,地下文学多用笔名――聊以禳祸耳,时代使然,身不由己。再举例说,说出这些话,则早被何必。何苦骂得狗血淋头也,则又系时代使然,身不由己也。信否?
燕子:鲁迅在国民党时代也有几十个笔名。
王怡:其实陈墨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笔名,他们是“以笔名行世”的一群人。除了署名之外,他们这些人在真实生活和几乎一切私人的非官方交往中也都使用这个自我命名。这就不能叫笔名了。所以我觉得关于姓名的历史真实性其实可以讨论。陈墨和他的本名陈自强这两个符号,到底哪一个是笔名,哪一个才是更真实的?后者除了有限的几个亲人,就几乎只在政府的户籍本上,在一切官方的档案中有效。我的看法其实那才是一个笔名。
刘帮:如果像鲁迅这么有名的作家,笔名与本名当然无所谓。但是,有几个写作者能够写到鲁迅那么有名呢?『野草』成员有二三十人,几十年百年之后,将来文学历史研究者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名字对照不起来了,小人物历史就会被大人物的历史淹没。
陈墨:我们几乎都是用的笔名,这也是我们三十年能够侥幸存在下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去年发生的事件,就是公安局查『野草』,只有殷明辉用的真名,而且注明在哪一条街道挂牌行医,所以公安局一下子就查到了他。
王怡:政治恐惧,是“以笔名行世”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通过自我命名,使自己的生命摆脱卑微的处境。换句话说,陈墨是一个有尊严的名字。陈自强则几乎不是。所以以后研究历史,文学史上存在过的那个人就是陈墨,而不是陈自强。或者说陈墨是历史,陈墨的本名叫陈自强才是野史逸闻。
燕子:请谈谈『空山诗选』-『野草』-『诗友』-『野草』的经脉。怎样的版本,有没有保存下来?
陈墨:1971年,在我的鼓动下,邓垦着手将诗友们的诗作编辑了一本『空山诗选』,这是一本手抄本。邓垦的字写的非常工整,一丝不苟,这本诗选就是由他抄写的。后来因为文字狱,他的夫人恐连累众诗友,遂将这本手抄孤本付之一炬。1976年,吴鸿又编了一本『空山诗选』,也因为文字狱之故,被迫将这本手抄孤本烧掉了。现在我们手中保留的文革时期的作品,多是互相手抄和传阅的,还有个人收藏的。 我们于1979年3月创办了『野草』,一共只办了三期。这三期是刻钢板油印的版本。第一期印了二百多份。第二期印了四百多份,第三期印了六百多份。每期十六页。今天赠送给你的是当时还未来得及装订成册的。 『野草』是成都地区第一份民间刊物。1979年3月5日晚由徐坯和邓垦张贴在成都两处繁华的街头――盐市口和总府街。还寄给了中宣部、文化部、胡耀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四川省委宣传部、成都市委宣传部、全国各大报刊和北大、复旦等著名大学以及艾青等人。 1979年11月魏京生入狱后,形势大变,我们决定『野草』以手抄小报的形式并更名为『诗友』继续办下去。从公开转到地下,从公开散发到内部传阅。1979年11月,邓垦手抄完『诗友』创刊号。第27期时,有人透露市委已查明『诗友』为『野草』的的易名的另一种形式,被定为“刊”。我们被迫停刊。1988年又恢复『诗友』,当时活动得最起劲的是孙路,“八九民运”中被捕入狱,『诗友』再次被迫停办。1990年10月『诗友』再次复刊,到1993年底共出总81期。1994年恢复『野草』原名,到2004年6月为止,共出92期。 燕子:印刷经费从哪里来? 陈墨:『野草』开始创办时,每人交经费五元。采购纸张、油墨各有分工,由我刻印创刊号蜡纸。
燕子:为什么『野草』八九十年代都没有出事,现在出事了呢?
王怡:从第89期开始,流沙河先生的夫人吴茂华老师参与编辑『野草』,我和廖亦武等人也给他们投稿,于是上面的人怀疑老右派与自由主义者合谋。准备出的第93期中,有我、廖亦武、余杰、流沙河等人的文章,我们打算在6月10日出一个关于张献忠入川大屠杀的专辑。有我的文章『大屠杀与外来政权――成都大屠杀360周年祭』。我们的文章有影射和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15周年的意思,刊物出来之前,已经有人拿到网上去载,但是6月9日,陈墨家就被抄,他的手稿、电脑、和来稿全部被抄走,至今未还。而且,还借他爱人有经济问题为名,逮捕了他爱人。陈墨在外面躲了几个月,刚刚回来。现在他爱人未被释放。我分析出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害怕『野草』从一个纯文学组织向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学组织转变。
陈墨:我们『野草』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坚持纯文学的原则,不应该发表时论、政论,不应该吸收王怡、余杰他们进来招惹当局,;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包括我在内,认为与其不死不活,发表不痛不痒的作品,赖活下去,不如吸收新的血液。而王怡、余杰他们的文章更加接近我们当初办『野草』的宗旨和风格。
王怡:也就是希望回到1979年的《野草》。
刘帮:现在『野草』的情况如何?
陈墨:几位成员到了美国,办了个『野草』的电子版。
刘帮:『野草』与独立作家笔会具有怎样的关系?
陈墨:我和蔡楚、还有另外一位,我们中的三人加入了独立作家笔会。在精神上,我与独立作家笔会的成员更接近。
燕子:我在阅读你们的作品时,有一个感觉,就是读不下去。好的文学作品应该经得起任何时代的考验,而不是某个时代或某个政权禁得住得。无疑,我们这一代受北岛们、舒婷、顾城们的“朦胧诗”影响很大,首先因为他们的语言艺术。即便你们的作品当时不是“地下”,而是“地上”,公开发表了,也不会引起反响。因为你们的直白式的文革式的表达,正是我们当时所要摒弃的。因此,你们的作品不光是你们命苦就不能发表。你们之所以在当时没有出来,恐怕文学作品本身有问题吧。 而且,我读你们的作品,好像并没有受到“新月派”的唯美主义影响,也没有形成一个文学流派。
陈墨:1983年,我开了一个小书店。那时九九已经定居香港,他给我们几个朋友带回一批原版的新武侠书籍。谁知好景不长,当局突然宣布“清除精神污染”,我被抓进派出所,挨了一顿拳足。幸亏邓垦诸友临危相助,至今终身难忘。另一文友,与我同样的罪名,被关了14个月。
燕子:你们的文学沙龙在谁的家?有无固定的场所?
陈墨:我们成都老百姓一般住的房子很小,没有客厅。一般我们聚集在茶馆。刚才谈到“书市”,后来我们『野草』的几个骨干,比如万一、冯里、谢庄等人就是在那时认识的。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书市”不仅满足了我们的求知欲,而且满足了我们的求友欲。因此,它也成了我们特殊的文学沙龙。风声紧时,我们就转移到离“书市”不远的“饮涛”茶铺,一边照常买书卖书换书,一边谈天说地、评古议今。后来,一些朋友下放当“知青”,我和九九去盐源彝族自治县当“饿农”,我们回成都的时候还是经常去茶馆,新南门的清和茶楼也是我们文革中常常去的地方。在那儿的交换写作的诗歌,讨论阅读的书籍。我自称为“茶铺派”,我的许多诗就是在茶铺里完成的。那时一杯茶才五分钱。五分钱可以泡一整天。
燕子:文革中茶馆没有关门吗?
陈墨:成都这个地方,不管时代发生怎样的政治变故或运动,老百姓,茶,照喝。文革“武斗”中最高潮的时候,茶馆也照开。
刘帮:听说您用卞之琳、李金发的名字写的诗歌,曾经以假乱真?
陈墨:我对朦胧诗的偏爱已久。1968年我着手编撰的『中国新诗大概选』时对“现代派”的收集与学习已经开始,那时也尝试写过朦胧诗,并且题上卞之琳、李金发的名字夹在他们的诗中间,居然还能鱼目混珠,让人莫辩真伪。后来不写了,一是悟到朦胧诗在这块土地上属于早产的贫血儿,且严重的水土不服,更重要的是,是悟到“确立自我、别模仿他人”的艺术真谛。
刘帮:您的老笔记本上的诗歌年月为什么是“1926年”、“1927年”、“1928年”?
陈墨:为避开“文字狱”。免遭杀生之祸。“1926年”就是“1966年”,“1927年”就是“1967年”,“1928年”就是“1968年”。
刘帮:你们大多是笔名,请详细注明你们的真名。再过几十年或百年,后人在研究这段文学史料时莫辩真伪了。
陈墨:我可以注明我们大家的真名。我的笔名除了陈墨、还有秋小叶、一丁、何必、也放等等几十个,一度还冒名徐志摩、戴望舒、朱湘、卞之琳等。或问:“一个苦力有这许多笔名,岂非画饼充饥乎?”答曰:“官方文坛多用本名,――直接受利,地下文学多用笔名――聊以禳祸耳,时代使然,身不由己。再举例说,说出这些话,则早被何必。何苦骂得狗血淋头也,则又系时代使然,身不由己也。信否?
燕子:鲁迅在国民党时代也有几十个笔名。
王怡:其实陈墨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笔名,他们是“以笔名行世”的一群人。除了署名之外,他们这些人在真实生活和几乎一切私人的非官方交往中也都使用这个自我命名。这就不能叫笔名了。所以我觉得关于姓名的历史真实性其实可以讨论。陈墨和他的本名陈自强这两个符号,到底哪一个是笔名,哪一个才是更真实的?后者除了有限的几个亲人,就几乎只在政府的户籍本上,在一切官方的档案中有效。我的看法其实那才是一个笔名。
刘帮:如果像鲁迅这么有名的作家,笔名与本名当然无所谓。但是,有几个写作者能够写到鲁迅那么有名呢?『野草』成员有二三十人,几十年百年之后,将来文学历史研究者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名字对照不起来了,小人物历史就会被大人物的历史淹没。
陈墨:我们几乎都是用的笔名,这也是我们三十年能够侥幸存在下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去年发生的事件,就是公安局查『野草』,只有殷明辉用的真名,而且注明在哪一条街道挂牌行医,所以公安局一下子就查到了他。
王怡:政治恐惧,是“以笔名行世”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通过自我命名,使自己的生命摆脱卑微的处境。换句话说,陈墨是一个有尊严的名字。陈自强则几乎不是。所以以后研究历史,文学史上存在过的那个人就是陈墨,而不是陈自强。或者说陈墨是历史,陈墨的本名叫陈自强才是野史逸闻。
燕子:请谈谈『空山诗选』-『野草』-『诗友』-『野草』的经脉。怎样的版本,有没有保存下来?
陈墨:1971年,在我的鼓动下,邓垦着手将诗友们的诗作编辑了一本『空山诗选』,这是一本手抄本。邓垦的字写的非常工整,一丝不苟,这本诗选就是由他抄写的。后来因为文字狱,他的夫人恐连累众诗友,遂将这本手抄孤本付之一炬。1976年,吴鸿又编了一本『空山诗选』,也因为文字狱之故,被迫将这本手抄孤本烧掉了。现在我们手中保留的文革时期的作品,多是互相手抄和传阅的,还有个人收藏的。 我们于1979年3月创办了『野草』,一共只办了三期。这三期是刻钢板油印的版本。第一期印了二百多份。第二期印了四百多份,第三期印了六百多份。每期十六页。今天赠送给你的是当时还未来得及装订成册的。 『野草』是成都地区第一份民间刊物。1979年3月5日晚由徐坯和邓垦张贴在成都两处繁华的街头――盐市口和总府街。还寄给了中宣部、文化部、胡耀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四川省委宣传部、成都市委宣传部、全国各大报刊和北大、复旦等著名大学以及艾青等人。 1979年11月魏京生入狱后,形势大变,我们决定『野草』以手抄小报的形式并更名为『诗友』继续办下去。从公开转到地下,从公开散发到内部传阅。1979年11月,邓垦手抄完『诗友』创刊号。第27期时,有人透露市委已查明『诗友』为『野草』的的易名的另一种形式,被定为“刊”。我们被迫停刊。1988年又恢复『诗友』,当时活动得最起劲的是孙路,“八九民运”中被捕入狱,『诗友』再次被迫停办。1990年10月『诗友』再次复刊,到1993年底共出总81期。1994年恢复『野草』原名,到2004年6月为止,共出92期。 燕子:印刷经费从哪里来? 陈墨:『野草』开始创办时,每人交经费五元。采购纸张、油墨各有分工,由我刻印创刊号蜡纸。
燕子:为什么『野草』八九十年代都没有出事,现在出事了呢?
王怡:从第89期开始,流沙河先生的夫人吴茂华老师参与编辑『野草』,我和廖亦武等人也给他们投稿,于是上面的人怀疑老右派与自由主义者合谋。准备出的第93期中,有我、廖亦武、余杰、流沙河等人的文章,我们打算在6月10日出一个关于张献忠入川大屠杀的专辑。有我的文章『大屠杀与外来政权――成都大屠杀360周年祭』。我们的文章有影射和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15周年的意思,刊物出来之前,已经有人拿到网上去载,但是6月9日,陈墨家就被抄,他的手稿、电脑、和来稿全部被抄走,至今未还。而且,还借他爱人有经济问题为名,逮捕了他爱人。陈墨在外面躲了几个月,刚刚回来。现在他爱人未被释放。我分析出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害怕『野草』从一个纯文学组织向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学组织转变。
陈墨:我们『野草』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坚持纯文学的原则,不应该发表时论、政论,不应该吸收王怡、余杰他们进来招惹当局,;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包括我在内,认为与其不死不活,发表不痛不痒的作品,赖活下去,不如吸收新的血液。而王怡、余杰他们的文章更加接近我们当初办『野草』的宗旨和风格。
王怡:也就是希望回到1979年的《野草》。
刘帮:现在『野草』的情况如何?
陈墨:几位成员到了美国,办了个『野草』的电子版。
刘帮:『野草』与独立作家笔会具有怎样的关系?
陈墨:我和蔡楚、还有另外一位,我们中的三人加入了独立作家笔会。在精神上,我与独立作家笔会的成员更接近。
燕子:我在阅读你们的作品时,有一个感觉,就是读不下去。好的文学作品应该经得起任何时代的考验,而不是某个时代或某个政权禁得住得。无疑,我们这一代受北岛们、舒婷、顾城们的“朦胧诗”影响很大,首先因为他们的语言艺术。即便你们的作品当时不是“地下”,而是“地上”,公开发表了,也不会引起反响。因为你们的直白式的文革式的表达,正是我们当时所要摒弃的。因此,你们的作品不光是你们命苦就不能发表。你们之所以在当时没有出来,恐怕文学作品本身有问题吧。 而且,我读你们的作品,好像并没有受到“新月派”的唯美主义影响,也没有形成一个文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