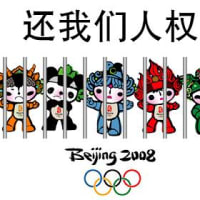那是一个歌颂副连长事迹的说唱台本。我不仅模仿报纸报道里的“闪光语言”,还对真人真事进行“升华”。我写道,迎着喷薄欲出的朝阳(不是阴冷的下午),副连长率领我们来到海边。他挺立队前,带领我们背诵毛主席语录,进行战斗动员(不是只做具体的实弹投掷准备)。他高声问战士,前方的靶子是什么(其实投弹无须靶子)?大家满怀仇恨地回答:那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好!”他下令:“狠狠地打!”——当然,此皆杜撰。我用劲咬着笔杆,要“挖掘”副连长的思想境界。我的处女作的标题是《一颗红心永向阳》。
是的,这是我的“红心”故事。了解“红心”和红色政治口号的生灭史,便不难理解,当我和我的同代人开始写作时,那些成为后人笑料的词语,何以会如此自然地出口成诵。这也是我走进文学和新闻的第一课。命运安排我,刚踏足这职业,就遇到“真话与谎言”这核心命题,只不过多年后才转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奋力前行,并付出代价。
其实也就在“红心”的传播到达巅峰的时候,我和许多同代人自己的心,已经悄悄变色。一九七〇年,我渴望入党而不获批准——因为父母随着文革深入成为“有问题的人”。到了一九七一年林彪“自我爆炸”,毛的神像在眼前动摇。
朱学勤曾说,林彪事件后公布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那些“恶毒语”,将他和下乡的同伴一棒喝醒,而乡间苦况和大饥荒史实,更将他们的左翼迷幻彻底轰毁。朱学勤在《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李“红心”的秘密》,讲了他的“红心”故事:
在他下乡的村子里,有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妇女队长。报纸记者来采访这位孤老婆婆,搜集了许多感人的事迹(朱回忆,事迹全部真实。如同我的副连长舍身扑救士兵,是让我铭记终生的真实情景)。但记者遇到难题:老人没有名字,像许多农妇一样,她的称呼也是“张王氏”、“李赵氏”之类。记者灵机一动,文章见报前给老人起了个名字:李红心。
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有人无意中窥见了“李红心”品质高尚的秘密:一天半夜,一位住在“李红心”家的女同学听见微弱说话声。悄悄起身,发现“李红心”一个人在屋里,右手在胸前划十字,口中喃喃自语。她在祷告!这位乐于助人的“李红心”婆婆,原来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林彪事件后,红色口号,尤其是发源于军队的一整套“高八度”语言,迅速降温。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传播强度,回落到一九六五年前的水平。一些新的口号——“反潮流”、“破法权”、“全面专政”开始风行。但“红心”犹在,仍配合着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林彪垮了,红心意味着“批林批孔当闯将”;邓小平倒了,红心又意味着积极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夜间,“深入揭批四人帮”成了红心的标志。毛泽东死了,报纸的大标题变成:《红心向着华主席》![20]
朱学勤说得对,“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看看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报纸吧:“几天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普遍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游行,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千万面红旗辉映着胜利的笑脸,千万颗红心发出了同一个战斗的声音:‘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21]
“红心”这个词,应当成为人类史的标本。它是强权的另一张脸,崇高而美丽。浸淫于简单化政治中的亿万人,数十年、无数遍口口相传,使这咒语迷幻力日。红心的“红”是形容词,更是动词,是强人驱动体制运转的动词。这就是为什么,被红其心灵的中国人会如此驯顺地缴出一切,利益与生命,常理与常情,还有爱和诚信。人们被诱导,震慑,裹挟——不只被领袖声威、党国大义,每一个人还被其他人——同学、同事、朋友甚至亲人所裹挟,被语言的声浪所裹挟,更被自己的羞耻感赎罪感所裹挟。“换心术”是暴君得逞一时的秘密武器。而“红心”的淡出,又恰是这三十年“中国奇迹”得以发生的玄机之一。
尽管在红色高棉和北朝鲜它还顽强存活着[22],但随着改革开放到来,“红心”一词在中国开始真正冷却了。就像在文革前反对“突出政治”一样,邓小平在文革后坚决抛弃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是邓的务实主义带给中国人的最重要转变,其意义绝不亚于告别饥饿。当然,历史的钟摆也开始强劲地摆向另一端。物欲横流,逐肉弃灵。是报应?
更确切说,“稳定压倒一切”的主轴下,即使越来越多人想找回各自的“心”,也并不受到嘉许。政治动员惯性犹存。“主义”不那么时兴了,可是精神驱使之速效,声音一致之便利,对政治家还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力。身居高位的大奸巨贪,也每每口吐红言。“红心”尚未绝迹。它的同义语——“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以治国”等新说法,仍飘来耳畔。然而时移世易,尽管权力还时有闯入人们内心世界的冲动,但已不再无所忌惮。真正的思想自由还在远方,但杂色斑斓的个人精神领域已经开始隐然成形。毕竟,“红心”等一整套政治话语,连同它们的语境、语义、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红”——崛起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民粹型极权主义政治文化——这个最根本的语源,彻底变异了。
有部国电影,名叫《Good-bye,Lening》(《再见,列宁》)。我对这块化石说:
别了,“红心”!
二〇〇八年清明写于香港大学
--------------------------------------------------------------------------------
[1] 人民日报1949.11.13 第5版,诗人柯仲平写道:“人民地球的心是颗大红心,我们能够拿红心团结全世界的人民”
[2] 《解放军文艺》1953.10 曾刊登《碧海红心》
[3] 解放军报 1958.04.06 第3版
[4] 人民日报1958.04.21 第4版
[5] 解放军报 1958.11.12 第3版
[6] 解放军报 1962.11.12 第4版
[7] 解放军报 1965.05.14 第4版
[8] 解放军报 1963.02.11 第2版
[9] 解放军报 1964.03.19 第1版
[10] 解放军报 1966.03.08 第1版
[11] 解放军报 1966.01.11 第1版
[12] 解放军报 1963.10.17 第4版
[13] 解放军报1964.01.18 第2版
[14]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和后来的现代京剧《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中都有“红心”,其中杨子荣“一颗红心似火焰,化作利剑斩凶顽”和李铁梅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的唱词尤其为人熟知
[15] 解放军报 1968.01.26 第2版
[16] 解放軍報 1968.06.02 第2版
[17] 解放军报 1968.01.07 第1版
[18] 解放军报 1968.02.23 第2版
[19] 解放军报 1967.07.21 第4版
[20] 解放军报 1976.12.13 第4版 华主席,即华国锋,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后任中共中央主席
[21] 解放军报 1976.10.24 第1版
[22] 在柬埔寨红色高棉,有小说《达姆彭的红心》;在北朝鲜,有歌曲《赤胆忠心 永葆红心》;一位金日成奖获奖作家写道:“我到祖国北部边陲看到豆满江水滔滔奔流,就联想起我国人民一片红心跟着金正日同志向前奔驰的洪流,闪出了诗情。”
是的,这是我的“红心”故事。了解“红心”和红色政治口号的生灭史,便不难理解,当我和我的同代人开始写作时,那些成为后人笑料的词语,何以会如此自然地出口成诵。这也是我走进文学和新闻的第一课。命运安排我,刚踏足这职业,就遇到“真话与谎言”这核心命题,只不过多年后才转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奋力前行,并付出代价。
其实也就在“红心”的传播到达巅峰的时候,我和许多同代人自己的心,已经悄悄变色。一九七〇年,我渴望入党而不获批准——因为父母随着文革深入成为“有问题的人”。到了一九七一年林彪“自我爆炸”,毛的神像在眼前动摇。
朱学勤曾说,林彪事件后公布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那些“恶毒语”,将他和下乡的同伴一棒喝醒,而乡间苦况和大饥荒史实,更将他们的左翼迷幻彻底轰毁。朱学勤在《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李“红心”的秘密》,讲了他的“红心”故事:
在他下乡的村子里,有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妇女队长。报纸记者来采访这位孤老婆婆,搜集了许多感人的事迹(朱回忆,事迹全部真实。如同我的副连长舍身扑救士兵,是让我铭记终生的真实情景)。但记者遇到难题:老人没有名字,像许多农妇一样,她的称呼也是“张王氏”、“李赵氏”之类。记者灵机一动,文章见报前给老人起了个名字:李红心。
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有人无意中窥见了“李红心”品质高尚的秘密:一天半夜,一位住在“李红心”家的女同学听见微弱说话声。悄悄起身,发现“李红心”一个人在屋里,右手在胸前划十字,口中喃喃自语。她在祷告!这位乐于助人的“李红心”婆婆,原来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林彪事件后,红色口号,尤其是发源于军队的一整套“高八度”语言,迅速降温。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传播强度,回落到一九六五年前的水平。一些新的口号——“反潮流”、“破法权”、“全面专政”开始风行。但“红心”犹在,仍配合着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林彪垮了,红心意味着“批林批孔当闯将”;邓小平倒了,红心又意味着积极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夜间,“深入揭批四人帮”成了红心的标志。毛泽东死了,报纸的大标题变成:《红心向着华主席》![20]
朱学勤说得对,“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看看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报纸吧:“几天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普遍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游行,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千万面红旗辉映着胜利的笑脸,千万颗红心发出了同一个战斗的声音:‘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21]
“红心”这个词,应当成为人类史的标本。它是强权的另一张脸,崇高而美丽。浸淫于简单化政治中的亿万人,数十年、无数遍口口相传,使这咒语迷幻力日。红心的“红”是形容词,更是动词,是强人驱动体制运转的动词。这就是为什么,被红其心灵的中国人会如此驯顺地缴出一切,利益与生命,常理与常情,还有爱和诚信。人们被诱导,震慑,裹挟——不只被领袖声威、党国大义,每一个人还被其他人——同学、同事、朋友甚至亲人所裹挟,被语言的声浪所裹挟,更被自己的羞耻感赎罪感所裹挟。“换心术”是暴君得逞一时的秘密武器。而“红心”的淡出,又恰是这三十年“中国奇迹”得以发生的玄机之一。
尽管在红色高棉和北朝鲜它还顽强存活着[22],但随着改革开放到来,“红心”一词在中国开始真正冷却了。就像在文革前反对“突出政治”一样,邓小平在文革后坚决抛弃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是邓的务实主义带给中国人的最重要转变,其意义绝不亚于告别饥饿。当然,历史的钟摆也开始强劲地摆向另一端。物欲横流,逐肉弃灵。是报应?
更确切说,“稳定压倒一切”的主轴下,即使越来越多人想找回各自的“心”,也并不受到嘉许。政治动员惯性犹存。“主义”不那么时兴了,可是精神驱使之速效,声音一致之便利,对政治家还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力。身居高位的大奸巨贪,也每每口吐红言。“红心”尚未绝迹。它的同义语——“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以治国”等新说法,仍飘来耳畔。然而时移世易,尽管权力还时有闯入人们内心世界的冲动,但已不再无所忌惮。真正的思想自由还在远方,但杂色斑斓的个人精神领域已经开始隐然成形。毕竟,“红心”等一整套政治话语,连同它们的语境、语义、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红”——崛起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民粹型极权主义政治文化——这个最根本的语源,彻底变异了。
有部国电影,名叫《Good-bye,Lening》(《再见,列宁》)。我对这块化石说:
别了,“红心”!
二〇〇八年清明写于香港大学
--------------------------------------------------------------------------------
[1] 人民日报1949.11.13 第5版,诗人柯仲平写道:“人民地球的心是颗大红心,我们能够拿红心团结全世界的人民”
[2] 《解放军文艺》1953.10 曾刊登《碧海红心》
[3] 解放军报 1958.04.06 第3版
[4] 人民日报1958.04.21 第4版
[5] 解放军报 1958.11.12 第3版
[6] 解放军报 1962.11.12 第4版
[7] 解放军报 1965.05.14 第4版
[8] 解放军报 1963.02.11 第2版
[9] 解放军报 1964.03.19 第1版
[10] 解放军报 1966.03.08 第1版
[11] 解放军报 1966.01.11 第1版
[12] 解放军报 1963.10.17 第4版
[13] 解放军报1964.01.18 第2版
[14]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和后来的现代京剧《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中都有“红心”,其中杨子荣“一颗红心似火焰,化作利剑斩凶顽”和李铁梅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的唱词尤其为人熟知
[15] 解放军报 1968.01.26 第2版
[16] 解放軍報 1968.06.02 第2版
[17] 解放军报 1968.01.07 第1版
[18] 解放军报 1968.02.23 第2版
[19] 解放军报 1967.07.21 第4版
[20] 解放军报 1976.12.13 第4版 华主席,即华国锋,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后任中共中央主席
[21] 解放军报 1976.10.24 第1版
[22] 在柬埔寨红色高棉,有小说《达姆彭的红心》;在北朝鲜,有歌曲《赤胆忠心 永葆红心》;一位金日成奖获奖作家写道:“我到祖国北部边陲看到豆满江水滔滔奔流,就联想起我国人民一片红心跟着金正日同志向前奔驰的洪流,闪出了诗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