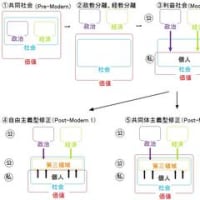二、关于言论自由
根据通常的政治学和法学理论,言论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与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言论自由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民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价值理念,是最基本的人权。其应有之义是每个人既有发表“正确言论”的权利,又有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只允许发表“正确言论”,不允许发表“错误言论”,就不能称之为“言论自由”),对于这项权利,公权力不仅不能干预,更不能剥夺,甚至不能审查,而应予以保护。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立法基础。而本案,行使公权力的一审法院在其一审判决中不仅干预、剥夺了刘晓波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而且还因刘晓波发表过的言论将其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这是对公权力的滥用,更是对“言论自由”常识的颠覆。
一审判决认定刘晓波实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的“罪证”是刘晓波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六篇文章及《零八宪章》中的某些“煽动”的言词,即一审判决所列举的:“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姑且不论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上述“罪证”绝对有“断章取义”,“肆意曲解”之嫌,仅从“言论自由”常识的角度也可以很容易的得出上述“罪证”只不过是刘晓波的主张和观点而已,其主张和观点的对错暂且不论,但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有何相干?具体而言:
(1)“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这段文字是刘晓波的文章《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的题目。从题目上可以看出,刘晓波写作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阐述自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见解。所谓“改变政权”并不是“颠覆政权”,二者并非同一概念,它们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每一届政府的更迭都可以解释为改变政权,只有通过暴力等非法手段推翻政权,才叫颠覆政权);而且法律也没有规定“改变国家政权罪”;(细读《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全文,可见刘晓波的主张是“不追求夺取政权的目标,而是致力于建设一个可以有尊严地活着的人性社会”,就可以清楚地得出刘晓波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一结论)。
(2)“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折断文字是刘晓波的文章《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中的半句话,原文是:“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民间尊严在观念上和法律上得以确立之日,就是国人的人权得到制度性保障之时。”刘晓波写作这篇文章是针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于2005年10月19日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发表自己的总结性的看法,而绝不是为了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自由中国只是对将来的一种展望,不含有任何颠覆国家政权的意思。(只要细读《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全文,而不是任凭一审判决中所摘录的片段进行判断,就可以清楚地得出这一结论)。
(3)“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是《零八宪章》中的两句话,原文是:“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零八宪章》中的两段话主要是提出开放党禁,和对祖国统一未来方案做出一种设想,而绝不是为了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不能由此得出刘晓波煽动他人去颠覆国家政权的结论。(只要细读《零八宪章》全文,而不是仅凭一审判决中所摘录的片段进行判断,就可以清楚地得出这一结论)。
从2005年以来刘晓波发表的499篇文章210余万字中挑选出六篇文章,节录出350余字,就认定刘晓波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难道不是对言论自由的极大嘲讽吗?
三、关于程序正义
严格遵守政党的法律程序,是实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享有正义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正如法谚所说: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即看得见的正义!这是每一位握有剥夺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裁判权的法官所必需牢记的!诸位法官亦不能例外;而一审判决对本案在侦查阶段以监视居住的名义对刘晓波变相羁押,审查起诉阶段不依法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庭审时限制刘晓波自我辩护及辩护律师的发言时间等严重违反程序的行为视而不见,不置一词,何谈程序正义?更遑论司法公正了!
辩护人坚信:刘晓波是无罪的,对刘晓波的任何有罪判决,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刘晓波二审辩护人: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尚宝军 律师
丁锡奎 律师
根据通常的政治学和法学理论,言论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与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言论自由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民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价值理念,是最基本的人权。其应有之义是每个人既有发表“正确言论”的权利,又有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只允许发表“正确言论”,不允许发表“错误言论”,就不能称之为“言论自由”),对于这项权利,公权力不仅不能干预,更不能剥夺,甚至不能审查,而应予以保护。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立法基础。而本案,行使公权力的一审法院在其一审判决中不仅干预、剥夺了刘晓波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而且还因刘晓波发表过的言论将其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这是对公权力的滥用,更是对“言论自由”常识的颠覆。
一审判决认定刘晓波实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的“罪证”是刘晓波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六篇文章及《零八宪章》中的某些“煽动”的言词,即一审判决所列举的:“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姑且不论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上述“罪证”绝对有“断章取义”,“肆意曲解”之嫌,仅从“言论自由”常识的角度也可以很容易的得出上述“罪证”只不过是刘晓波的主张和观点而已,其主张和观点的对错暂且不论,但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有何相干?具体而言:
(1)“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这段文字是刘晓波的文章《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的题目。从题目上可以看出,刘晓波写作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阐述自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见解。所谓“改变政权”并不是“颠覆政权”,二者并非同一概念,它们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每一届政府的更迭都可以解释为改变政权,只有通过暴力等非法手段推翻政权,才叫颠覆政权);而且法律也没有规定“改变国家政权罪”;(细读《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全文,可见刘晓波的主张是“不追求夺取政权的目标,而是致力于建设一个可以有尊严地活着的人性社会”,就可以清楚地得出刘晓波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一结论)。
(2)“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折断文字是刘晓波的文章《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中的半句话,原文是:“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民间尊严在观念上和法律上得以确立之日,就是国人的人权得到制度性保障之时。”刘晓波写作这篇文章是针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于2005年10月19日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发表自己的总结性的看法,而绝不是为了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自由中国只是对将来的一种展望,不含有任何颠覆国家政权的意思。(只要细读《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全文,而不是任凭一审判决中所摘录的片段进行判断,就可以清楚地得出这一结论)。
(3)“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是《零八宪章》中的两句话,原文是:“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零八宪章》中的两段话主要是提出开放党禁,和对祖国统一未来方案做出一种设想,而绝不是为了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不能由此得出刘晓波煽动他人去颠覆国家政权的结论。(只要细读《零八宪章》全文,而不是仅凭一审判决中所摘录的片段进行判断,就可以清楚地得出这一结论)。
从2005年以来刘晓波发表的499篇文章210余万字中挑选出六篇文章,节录出350余字,就认定刘晓波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难道不是对言论自由的极大嘲讽吗?
三、关于程序正义
严格遵守政党的法律程序,是实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享有正义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正如法谚所说: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即看得见的正义!这是每一位握有剥夺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裁判权的法官所必需牢记的!诸位法官亦不能例外;而一审判决对本案在侦查阶段以监视居住的名义对刘晓波变相羁押,审查起诉阶段不依法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庭审时限制刘晓波自我辩护及辩护律师的发言时间等严重违反程序的行为视而不见,不置一词,何谈程序正义?更遑论司法公正了!
辩护人坚信:刘晓波是无罪的,对刘晓波的任何有罪判决,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刘晓波二审辩护人: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尚宝军 律师
丁锡奎 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