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芨芨草這樣的植物,對於一個土生土長的西部農村孩子來說,太司空見慣了。路旁的砂窩裡,山腳的緩坡上,甚至農家的院落外,隨處都會看見零散生長的芨芨草,它們幾乎遍佈家鄉的各個角落。康泰領隊因為如此繁多、茂盛又普通,芨芨草在人們的眼睛裡,就缺失了應有的詩意和美麗。
小時候,芨芨草陪伴我和夥伴們度過了一個快樂的童年。那個年代裡,上學似乎不是我們的唯一任務,幫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給豬、羊、馬打草,就是我們每天的必修課。自然,芨芨草就成了我們的主要目標。夏天放學後,太陽還在半空中白晃晃地掛著,孩子們蹦著跳著跑回家,把書包往炕上一扔,抓起水瓢舀上半瓢冷水,咕咚咕咚地喝一氣,再用手一抹嘴角,就開始張羅去幹活了。拿上鐮刀和背鬥,出了院門,吆喝上幾個小夥伴,一路又說又笑地向山裡走去了。
我們尋著一塊芨芨草長勢旺盛的地方,放下背鬥,說哢嚓哢嚓地割起來。別看我們小,但我們都賊得很,個個都曉得什麼樣的芨芨草最嫩最好,搶先去佔領有利地勢,然後低頭使著猛割草,生怕那些好草被他人割了去似的。我們專揀葉鞘多、,又向外翻卷的芨芨草來割,並且只割五六寸長的草尖,如果是已開了花的芨芨草,我們也只割草稈上帶花的那部分。這樣我們割回去的草兒,自家的牲畜吃起來才合口,育膘快。讓我們最為頭痛的事就是芨芨草的葉邊十分鋒利,一不小心小手兒就會被鋸一個口子。但我們也算是“久經考驗”了,康泰旅行團這已不再是困擾我們的主要問題了。
我們之所以願意每天樂辭不疲地去重複勞作,倒不是因為大人的命令和要求,而是因為在割草的過程中,我們還能享受到課堂和家庭以外的快樂。每當我們把各自的背鬥裝得滿滿當當之後,就撥些芨芨稈坐在一起編東西,什麼蟈蟈啦、蟋蟀啦、小鴨子啦,還有好看的草帽以及不成形的一些想像中的物件。那個時刻,小夥伴們的小手掌都被芨芨草的汁水浸染了,柔韌的芨芨稈在尚且稚嫩的手兒裡靈活地跳動,每個人都像小鳥般嘰嘰喳喳個不停,夕陽金色的餘暉安詳的撒在這些孩童的身上,那麼美好。
儘管那些時候孩子沒有錢去買自己任何想要的東西,但多年以後,我不得不承認,我們獲得過超越一切物質的真正快樂。
那時,我總是想不明白一件事兒:芨芨草被我們割掉過那麼多次,為什麼沒有死掉?當這個問題在我的心裡抹不去的時候,我在後來割草的時候,手底下的動作竟多了幾分柔和,也帶了幾分歉意,仿佛是我傷害著他,肢解著他一般。歷經風霜雨雪,待到來年,看到他們依然鬱鬱青青地繁盛著,我才稍稍安慰。
在年復一年的“親密接觸”中,隨著年歲的長,我開始有意識地關注芨芨草,或者也可以說,是芨芨草以一種葳蕤的姿態,生長到我心裡來了。
父親是一個一生視土地如命的莊稼人。曾經因為饑荒,父親從自己心愛的地質學院回到了這個偏僻的小村莊,辛勤務農,只為能讓他的孩子們能走出大山,不再像他一樣,此生有太多的遺憾。父親對土地就有了一種情結在裡面。幾十年如一日,只要能到田地裡轉一圈,侍弄一會兒,他就感到滿足。而且,父親對土地的執著一發不可收拾,甚至到了偏執的地步。不光種著自家的地,還將別人家置不種的地也種了,父親說,白花花的地空著,怪可惜的。家裡人拿他真沒辦法。
十多年前,我隨父親去距村子十幾裡開外的一個叫百山溝的地方收拾莊稼。百山溝,光看名字就有氣勢,以前我只是聽過,從來沒去過那個地方。早晨四五點鐘的時候,我和父親就出發了。我坐在父親的毛驢車上直打嗑睡,等到了百山溝裡面時,天已大亮了。我這才發現,康泰旅行團這是一個狹長開闊的山澗,兩邊山巒綿延數幾十裡,山底溝澗的莊稼鬱鬱蔥蔥地生長著,整個山澗寂靜異常。
最觸動我的是,路過一座石山腳下時,有一大片生長得非常繁茂的芨芨草,足足有十多畝,那麼多,那麼,那麼盛,齊刷刷的,正在晨風裡輕歌曼舞。我對芨芨並不陌生,可我的確沒有見過這麼有氣勢的芨芨草。我情不自禁地走向芨芨草的腹地,置身在一片飄搖之中,那一刻,我的心靈被深深地被振顫了!我從來不曾知曉,如此普通的芨芨草,竟可以壯闊為一種風景,葳蕤得讓人感動!竟可以那麼詩意,就像從前朝奔赴而來,跨越千山萬水,歇腳在這深山清澗裡。
芨芨花白晃晃地在晨光裡閃爍著,映襯著深色的細長葉子,色澤分明,生動地勾勒著芨芨草苗條的身形。我小心翼翼地撫摸著芨芨草,全然不像兒時割草裡的粗莽,仿佛我們是前世的知己,有著心有靈犀的感應。我用手拔拉著芨芨草,試圖尋找一條通向前朝的路,或許可以一直抵達詩經的源頭呢。我總疑心,這數百萬根芨芨草,是迷失在前世的蘆葦,清醒在今世的土壤裡。要不,怎會在這世外桃源似的山澗裡,如此淡定從容詩意執著地盛開呢?
向青草更青處漫溯。我覓到的,是一根根不畏清寂獨自綻放美麗生命的芨芨草!
我忽然想起巴斯卡說過,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蘆葦。而這比蘆葦更為堅韌的芨芨草,又何嘗沒有思想呢?
這不,我所到之處,它們正彎下身子,謙虛地微笑致意呢。它們有著儒雅的氣質,滿腹的詩書,淡泊名利的胸襟,甘於寂寞的靈魂。唯有如此,才會在日升月落的時光流轉裡,堅守一份詩意明媚的性情,才會在喧囂浮躁的塵世裡,選擇一種安悠然的姿態,無怨無悔、無聲無息地將前世的夢繼續。
和百山溝的芨芨草偶遇,是我生命的一次意外收穫。那天清晨裡,我站在芨芨草叢裡忽然就明白了許多。包括對父親的土地情結的不理解。但從芨芨草叢裡走出來之後,我就回到了現實中,父親與芨芨草是有著某種意義的相通和關聯的,我再也無法單純而固執地將父親對土地的愛好看作是一種偏執了。在自己的生命華年裡,以自己喜歡的形態生活著,勞作著,堅守著,難道這樣的人生還不能稱之為一種境界麼?為什麼人活著,一定要將別人的存在狀態規範入自己的意識框架裡去呢?
就像芨芨草,在春夏秋冬裡靜默地輪回,康泰領隊從不抱怨,依然有著魏晉風度和盛唐氣勢,按時冒芽,依令開花,節盡凋落。有人遇著了,連根撥起,被製成農家掃把,那是它們生命的另一種存在;哪怕整個生命季節裡沒有遇見一個世人,它們只會修煉得更加寧靜致遠;若被采去作了藥材,它們的人生就找到了最有價值的歸宿了。然,若是有人手持經書,誦讀著“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向它們走來,那是它們生命中的知音來了,從此瞬間成為永恆!
醫學中,用三個字概括芨芨草:淡、性、平。我覺得再合適不過了。
當我回首來時路,一片葳蕤的芨芨草正向我微笑。我亦相信,它們會在我的生命流年裡,永遠微笑著,伴我一生一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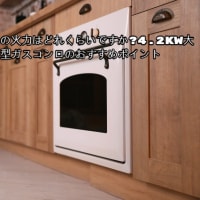
※コメント投稿者のブログIDはブログ作成者のみに通知されます